李建华 张善燚-市场秩序、法律秩序、道德秩序
李建华 张善燚 (此文发表于《哲学动态》2005年第4期)
代市民社会的勃兴开始了现代社会的多元发展进程。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之上,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三大基本领域或三大基本层面: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显现出了开放、自由的特征,从而也使人类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或经济文明、政治文明或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又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对于这些社会成果,则必须由社会秩序加以维护和保障。而且,在社会转型时期,要实现社会生活的有序化,同样存在由秩序的优先选择到秩序的系统选择问题。建立“和谐社会”,就是社会系统性的价值选择。
一
所谓秩序,指的是在社会进程中都会存在的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有按照有序模式存在和运作的倾向;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已表明,凡是在人类建立政治或社会组织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这种要求确立社会生活秩序模式的倾向,并不是人类所做的一种任意专断的努力,而是根植于社会结构之中,特别是经济秩序之中。
现代社会是由传统社会转型而来的。在传统的小农经济时代,也存在着经济秩序,但由于当时实行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自我生产、自我消费的经济特征使社会成员处在封闭的地域之中并主要以家族关系来维系相互的存在,因此其经济秩序被亲缘伦理秩序所替代,未能真正地发挥作用。到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市场为本位进行经济交往和商业往来,社会资源也是通过市场来进行配置,才使市场真正发挥了作用。在市场经济中,市场通过其“看不见的手”来调配各种社会关系,使所有的物品和劳务都按市场价格自愿地以货币进行交换,使社会资源能充分发挥尽可能大的效益,从而形成了真正的市场秩序。
一般而言,市场秩序并不等于简单的微观市场交易规则,也不同于社会交易的规制化,市场体系的建立并不一定意味着市场秩序必定会出现。市场秩序是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利益和谐、关系和谐、收益共享、竞争适度、交易有序、结构稳定的状态。[1]市场秩序作为一种利益共享、合作且富有效率的秩序,意味着这种秩序最终的目标在于,为社会分工、社会协作、社会交换和社会创新创造一种合作、竞争、和谐的环境,以便经济主体能够在合作中创造共享的利益。市场秩序作为一种利益和谐的秩序,主要集中体现在国家能够满足政治主体利益最大化的规则系统与保证长期持续经济增长的规则系统相一致。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实现具有不同的模式,但不会出现政治力量严重侵蚀经济系统,导致政府与民争利、在制定规则的同时破坏规则的情况,因此,市场秩序在本质上应是具有法治的秩序。市场秩序作为一规则约束下的自由秩序,体现为交换的自由、合作的自由及选择的自由,各种市场经济主体都可以根据自己符合规则的偏好和利益做出自己的决策,而不受制于其他任何主体。市场秩序作为一种不断扩展的秩序,在于市场秩序的自由特征能产生的巨大包容性,因为市场秩序所营造的私人自由空间使它能够充分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并将所有可以创造经济收益或有交换价值的对象都纳入这个体系之中。总之,市场秩序在本质上是一种富于理性的、稳定的、自由的、可扩展的利益共享秩序。在此意义上,市场秩序与现代法律秩序、道德秩序是同源同质的。
当然,在实际生活和生产中,市场秩序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因为没有一种经济形式能够完全依照“看不见的手”的原则顺利运行。由于市场经济具有某些内在的缺陷,通常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形成垄断的可能。当经济活动存在显著的规模性时,生产厂家必然尽量扩大生产规模以实现最低的生产成本。市场秩序下激烈竞争的结果,可能形成独家经营的垄断局面。在垄断的情形下,厂商为了获得高额利润,生产的产品量往往少于社会需要量。另外,即使存在技术改革、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可能,垄断者也会因缺乏改革的动因而未必从事改革。(2)市场外部性。市场外部性就是市场本身不具有而又无法排除的外部影响。只要经济活动存在外部效果,就会影响市场秩序,因为这些外部性因素往往没有或者不可能被计人决策的依据中去。例如,某工厂排出大量废渣、废气、废水,就是有害的外部效果。经济发展中的外部性对市场秩序建立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生态问题、失业问题、分配不公问题等。(3)分配的不平等性。市场秩序的作用,将会使因个人能力与经济状况的差异所带来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因而使人们拥有财富的差距也愈来愈大。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造成了社会存在巨大的贫富悬殊,私有制与保护剥削固然是其制度性的原因,而市场机制的这一缺陷也是原因之一。一般来说,市场秩序可能取得效率,但在不同程度上会影响到公平原则,从而影响市场的竞争。
为了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不足之处,就必须发挥政府的职能,通过法律秩序来维护市民社会的进步、法律在本质上就是通过限制特权的行使,对社会市场失灵的干预和修复。法律的目的是制定各种法律规范,把有序关系引入私人和群体的社会交往以及政府机构的运作之中,从而形成法律秩序:法律秩序具有连续一致性、普遍性、明确性的特点,并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调和经济愿望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从而保证了各种关系的协调和有序。不过,创制法律秩序在满足社会和经济生活和谐的同时,也必须谨防法律秩序由于其过于具体、明确,而导致社会受到法律秩序的刻板约束和时滞现象的发生,为此,道德秩序不可或缺。
二
法律秩序赖以作用的法律规范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由国家机关制定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社会行为规范:虽然从形式上看,它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化规范,而道德秩序规范则是非强制性、非制度化的,但就其实质内容而言,二者都是社会秩序文化的主体,都是适应人类社会生活而产生的:并且,法律秩序来源于道德,以道德为根基形成、生长,正因为如此,法律天然即具有一种道德属性,在其形式的外壳之下,流动着伦理的血液。[2]在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中,那些有利于社会、国家的行为被指定为义务,那些能给行为主体带来利益的行为被规定为权利;对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加以禁止,对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加以肯定。可以说,一切社会价值观念都需要借助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引申为人们“应如何行为”的行为指向,从而具体指导人们的行为.实现社会所需要的价值目标。
法律规范固然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但必须关涉人们的道德取向、道德风俗、道德习惯等各种因素和成分。它以人们所能接受的道德规范为基础,集中体现人们的利益和愿望;因此,法律秩序之应然是建立在道德之应然基础之上的,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具有内在的同构性。那么,道德秩序所体现的内在精神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种内在精神就是对人生价值和社会理想的崇高追求。理想性是道德的灵魂。道德秩序的精神总是以“应然”的价值指令把社会生活引向理想的层次,具体包括生活的幸福、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秩序的稳定等,同时也包括人类追求崇高精神价值的超越性。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道德秩序,但是道德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和人类社会对共同利益的追求决定了共同的精神理念的存在,如正义、秩序、利益等。历史上,思想家们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长久不衰,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现代的西方思想家,正义问题始终是其思想主线和主题之一,并Ek"没有任何其他问题能引起人们如此热烈的争执,[3]但遗憾的是人们至今还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而只能尝试更好地解释这个问题。因为正义是一个最为崇高但又最为混乱的概念,从古至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传统的思想家从道德的角度对正义进行了不同的诠释,曾赋予它自由、平等、幸福、安全、和平、秩序、利益等不同的观念,使“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 Proteanface)[4]。应该说,上述各种观念都有符合人的本性和本质的正义的方面,但最能体现正义性质的则是平等和自由。平等最先由亚里士多德做出系统阐述。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寓于“某种平等”之中,平等是正义的尺度。他把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两种,其中的分配正义即机会平等。这种平等的理念对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深层价值观念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自由在正义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许多思想家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家都认为与正义观念相联系的最高价值就是自由,如斯宾塞和康德的正义概念就是以自由为核心。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被看做是最高的正义。
道德秩序不但表现了自由、平等、正义等精神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人类的价值追求。人类总是希望生活在有秩序的环境之中,而道德规范即是这种价值追求的产物。因此,道德一经产生,即具有秩序理念。它作为一般的、普遍的社会调控手段,总是力图防止社会混乱,使社会永远处于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状态之中,以达到理想的社会“大治”。道德秩序之精神从更深层次上分析,它是人类利益关系的产物。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但利益问题如何表现为道德问题?利益关系的处理如何表现为一种道德秩序?就利益的产生机制而言,利益产生于人的需要,人有什么需要,就会有什么样的利益;人有什么样的利益,就会有什么样的道德,在此意义上,道德秩序就是“心灵秩序”,就是“心性秩序”。只要心性圣洁,就能使道德有序,中国古代由孟子开创的心性伦理,就是这样的理论路径。就利益的实现机制而言,主要看目的和手段,即人需要什么,是没有道德可言的,因为欲望本身不是利益,只有当欲望现实化时才有利益问题,才有道德调节的必要。所以,现代道德秩序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利益而不是压制利益,它越来越不同于传统的心性伦理秩序,而趋向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秩序。耶林主张,人的行为的目的在于保护社会生活条件,社会生活条件就是利益,这里所指的利益表现为“善”、“真”、“美”。因为人的天性在于追求“善”、“真”、“美”,也即谋求利益,所以人类活动应以道德为基础,从道德原则出发以增进道德利益。边沁主张立法应以增进人类的幸福快乐为目的,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最大道德利益。这些精神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的社会与人伦关系的共同认识,如果一旦丧失了理想性和精神崇高性,道德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因此,道德秩序的理想精神是伴随道德发展的历史轨迹而始终存在的。
三
道德秩序的这种内在价值精神不仅使道德秩序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而起作用,而且又成为各种法律秩序形成的价值参考。柏拉图就是通过道德理念来寻求正义的理想国的,他认为“正义的原则是国家的基本法”[5]。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时候,通常会怀着一种美好的愿望和祈盼,将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追求赋予法律,这种取向和追求暗含的就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法律中的理想的、永恒的法本体即法律精神。法律精神也蕴含了人类对正义、秩序和利益的追求。不过,在具体的立法过程中,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不同意识形态对立法者造成的影。向,使立法者必然要充分考虑各种现实的要求,以及自身的需要,因而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立法原则体现的不再是道德理想,而是法律意志,这种法律意志昭示的是出于统治意志的法律秩序而非道德秩序。
首先,作为法律精神的意志虽然和正义联系在一起,法律包含着自身的正义标准,但这种正义是合法律性的,凡是背离法律或违背主权者意志的就是非正义,但合法律性不是政治合法性的惟一标准,还需有合道德性和合公益性。在政治权威的影响下,法律有可能是正义的,但这里所体现的正义是政治意义上的正义,而非道德上的正义。所以,在此意义上,实体法符合正义,法律主权意志只要忠实地运用其实在命令以保护现存法律,就是正义,但这种正义有可能因为道德精神的缺失而成为非正义。当一个社会的法律背离了德性的时候,往往就成为了专制的工具。
其次,在现实生活中,要实现司法的合法律性以及政治正义,法律理念就须以秩序作为其得以存在和表现的形式。这里的秩序具体体现为国家强制性,通过国家强制性,使社会民众在国家控制的范围之内生活和行事,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秩序。作为近代实证法学派发展链条中的一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赞同法的意志说。马克思与恩格斯都系统论述过法律精神,认为它不仅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且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进一步从经济、社会角度来阐述法律秩序,认为法律所体现的阶级意志的内容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这就最终把法律秩序看做是一种利益,但这种利益是经济利益而非道德利益。可见,以道德精神为源泉的法律秩序与道德秩序并不等同,它是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全面考虑现实需要的理念,深深地烙上了政治、经济、社会的具体要求;
当然,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差异仅仅只是形式上的,不论是道德正义、秩序、利益还是政治正义、社会秩序、经济利益,它们在本质上还是一致的。法律秩序如果不体现道德秩序的精神,甚至背叛道德秩序的精神,就是不义之法律秩序。不义之法律秩序尽管可以凭借国家权力得以产生,但无法有效地维护和促进社会的发展。因为不义之法律秩序不仅是法律本身背离了人类的道德秩序之精神.而且也是对法律精神的背叛,是道德与法在深层次上的冲突;这种冲突一方面表现为社会道义对法的抗拒。如果一种法仅仅表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而置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顾,置社会发展的趋势而不顾,置百姓的生活安定和幸福而不顾,社会公众就会表现出激烈的否定态度:另一方面,表现为执法者的良心对法的抗拒。作为一个有着良好道德的执法音,一旦庄理性上认识到了他所执行的某些法律的不义性质,必然会在执法者内心产生道德与法的冲突和斗争:这时道德与法律谁胜谁负,完全取决于执法者的道德信念坚定与否、社会道义的支持是法律实施成为可能的“外在道德性”,执法者的道德良心成为法律实施的“内伍道穗性” 按富勒的区分,前者是一种义务的道德,后者是一种愿望的道德。[6]
其实,社会道义和义务是有区别的。社会道义是道德价值的社会趋向及其大众表现,而义务是对社会道德要求的个体意识和自觉承受。社会道义是个体道德责任意识的一种群体整合,往往表现为强大的社会舆论威慑力,可以说正义感就是社会道义的一种义务化。如果说法律秩序是对人的行为的外在约束,道德秩序就是一种内在约束。它们作为秩序文化的主干,法律秩序只不过是道德秩序等内在约束的外在表现。倘若没有“内在约束”的需要,则“外在约束”的建立也就失去了根基。在现代社会,失去“内在约束”的法律秩序甚至会成为专权的任意工具。尽管西方的自然主义学派和实证主义学派观点迥异,但它们绝大多数还是为法律秩序提供了一种价值判断标准。因为“合法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法律的发展”,而“法律的发展小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7]现代法治社会,国家主权已由君主回归民众,法律不再是主权特权的权威延伸工具,因而法律的价值评判标准必须建立在广大民众理想的正义、秩序和利益的道德价值基础之上。但是,“法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的发展,事实上既受特定社会集团的传统道德、理想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一些个别人所提出的开明的道德批判的影响。”[8]仍有些立法者会根据自身或集团的需要将其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使法律秩序成为其为所欲为的手段。法律由于找不到价值根基而陷入盲区,蜕变为简单的专政工具。可见,确立法律秩序的伦理基础和原则是维护法律根本属性和实现民主法治的必要条件。
总之,社会生活的有序化是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但如何实现社会生活的有序化,以什么秩序作为治理的目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市场秩序从社会的基础层可以保证经济生活的有序化,但不足以使社会实现公正、和谐的目标;法律秩序有效地保证了社会的制度供给,但无法使人的心灵得到应有的安顿;道德秩序是一种利益关系的心性和谐,但离不开经济的支撑和法律的保证。市场秩序、法律秩序、道德秩序在现代社会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纽带,单一的秩序追求只能使“纽带断裂”而形成“松散”的社会结构,最终导致社会的畸形发展。
【注释】
[1]纪宝成:《论市场秩序的本质和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胡旭晟:《论法律源于道德》,《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年第4期。
[3]HansKelsen,What’s Justic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7,P.267.
[4)[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第252页。
[5]Plato,The Republic,Anchor Books,1973,pp.341—342.
[6]戈尔西著,齐海滨译:《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第4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杜,1976,第352页。
[8][英]哈特著,张文显译:《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第182页。
【作者简介】
李建华,中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善燚,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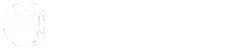



 客服1
客服1  客服2
客服2